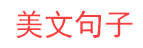名句:客来满酌清尊酒,感兴平吟才子诗。

《第七天》是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余华继《兄弟》之后,时隔七年后最新长篇小说。用荒诞的笔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讲述了现实的真实与荒诞;讲述了生命的幸福和苦难;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比恨更绝望比死更冷酷的存在。
《第七天》借助一个死人赴死的魔幻故事外壳,将一段衍生于中国当代的残酷写真展现了出来。用文艺作品触及读者的心头之痛似乎并非多有难度之事,而是在触及之后还要留有余响和余震则变得凤毛麟角。《第七天》中的“我”在餐馆吃饭意外死亡,揭示了一种唐突的、贸然的命运降临,它不寄托于非凡或者离奇的生活,而是对苦命的一种无可奈何。而这如何造成的,以及现实对悲剧性命运的反馈又是如何影响的,我们的作家连追问和冒犯的心思都没有,在残酷而凛冽的现实面前,自己的意志力和能力已率先被敲打得七零八碎。
余华第七天小说名《第七天》确实源自于圣经的《旧约·创世记》,“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但内容与圣经无关,她说,这是一个很残酷、但又很温暖的故事,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正如余华所说,“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
余华的第七天里有这段话吗?无论多么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无论...余华第七天里没有看到,而且这种治愈系的文字实在不像是余华写的,好像是出自王小面《世界上唯一的你》
余华写的第七天的全文概括《第七天》选择一个刚刚去世的死者“我”(即杨飞)作为第一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1333431353931人称叙事者,由“我”讲述死后七天里的所遇、所见、所闻之事与往事,“我”力所不及的一些故事或故事片段则蝉蜕给与“我”相关的他者,由他者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所遇、所见、所闻之事与往事。
主人公杨飞是主环,这一主环分别连套一些不同的次环,次环又连套次次环,从而形成多重连环式结构模式。
分别是杨飞——李青——李青的后夫,杨飞——杨金彪——生父生母一家,杨飞——杨金彪——养父兄弟姊妹,杨飞——鼠妹与伍超——肖庆,杨飞——李月珍夫妇——杨金彪,杨飞——李月珍夫妇——二十七个婴儿等均构成一个个三连环结构。
三连环结构涉及第一人称蝉蜕叙事。所谓第一人称蝉蜕叙事是指由第一人称叙事者“我”蝉蜕到下一个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叙事者的叙事方式。
杨飞到“死无葬生之地”后不久,遇到“我”出租屋的邻居“鼠妹”,她认出新到的防空洞地下室的鼠族邻居肖庆,肖庆为大家带来了“鼠妹”的男朋友伍超在阳界的消息。
于是,故事的讲述者就由杨飞蝉蜕到“肖庆”,然后“肖庆”以第一人称为大家讲述“妹”到“死无葬生之地”后大家所不知道的关于伍超的故事。
扩展资料:
《第七天》广泛涉及官僚腐化、官民对立、贫富分化、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暴力执法、食品安全、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城市鼠族等各阶层各方面的问题,其通过杂闻的“信息价值”和隐喻功能来对当下政治发言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第七天》体现了余华对现实的焦虑和绝望,他对现实中的欲望、混乱、不公平和弱肉强食的极度愤怒。洪治纲认为,余华采用了“用死者来观看生者”回避了正面叙述的尖锐性。
《第七天》采用的社会新闻正是当下社会或刚刚谢幕或正在上演的景观,其荒诞之程度远远超乎作家的想象,作家又何必再费心思编造情节。把杂闻原样照搬进小说文本,迅速编织出小说文本的当下背景,使小说文本具备了与当下社会共在的现场感,使其与社会文本的对话在同一个舞台展开。
余华的第七天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讲了男主角死后七天的各种遭遇和回忆,里面有很多沉重的社会问题,男主角回忆自己出生被捡到抛弃回归成长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植入了系列社会问题如丧葬强拆爆炸案等等,耐人寻味
《第七天》好词好句好段1.我的身体摇摇晃晃坐在那里,像是超重的货船坐在波动的水面上。
2.我的身体像是一棵安静的树,我的记忆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马拉松似的慢慢奔跑。
3.我们同时站了起来,刚才已经稀少的雨雪重新密集地纷纷扬扬了。她挽住我的手臂,仿佛又一次恋爱开始了。
4.如果你的世界,没有痛苦的害怕,没有尊严的担忧,没有富贵的贫贱,没有暖寒的交替,没有外貌的困扰,没有男女的区别,没有你我之分,没有生死顾虑,你才会离"真正的活着"越来越近。
5.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
6.我的悲伤还来不及出发,就已经到站下车。
7.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8.我不怕死,一点都不怕,只怕再也不能看见你。